在各路资本竞相逐鹿机器人产业的热潮下,机器人产业泡沫化正在引发人们的担忧。
不过,常州金石机器人的创始人刘金石却显得很乐观,“因为在关键零部件上并不受制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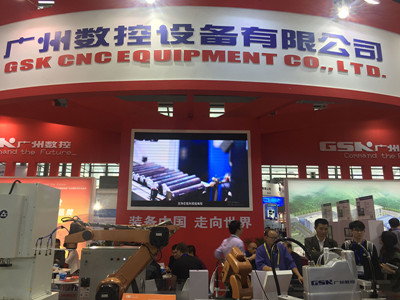
图片:数控机床市场网
传统关节机器人(即机械手臂机器人)需要三类核心零部件:高精密减速机、伺服电机和控制系统。其中,高精密减速机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在一台六轴的多关节机器人中,高精密减速机在整个机器人成本里占到30%或者更高。”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宋晓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部分世界市场长期被日本企业纳博特斯克所垄断,该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精密减速机制造商,“他们的减速机,卖给中国企业价格是卖给日本、德国等同类企业价格的五到八倍。”
从技术路线看,金石机器人“另辟蹊径”,主攻桁架机器人,这是一种有别于关节机器人的直角坐标机器人,非常适用于金属加工类的数控机床自动化和重载高速搬运行业,可以为“无人工厂”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在这种技术路线下,高精密减速机并非核心零部件,也不会受制于国外企业。
不过,对于这家成立近7年的企业来说,如何挤进被国外高端品牌长期占据的市场,真正跨越盈利障碍,仍然是考验。公司在2016年挂牌新三板,公告显示,2014年度、2015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6096.19万元、5197.32万元,但尚未实现盈利,净利润为-115.61万元、-722.45万元。
这也是很多国产机器人品牌面临的共同难题。2013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市场。201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是6.9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将近30%,但国产品牌仅占到中国市场销量的7%。
政府部门期待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能复制“中国高铁”模式,未来以自主创新换市场。不过,与高铁技术集中在几家大企业手里不同,“在机器人这个领域,有高端产业低端化和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的风险。”在今年“两会”期间,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如此提醒。
技术路线另辟蹊径
在“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政策利好的刺激下,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正在经历井喷式增长。
“机器换人”正在成为当下制造业最火热的话题,也是大势所趋。
国际机器人联盟(IFR)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工厂使用的机器人数量将超过其他国家,但在机器人密度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目前在中国制造行业中,每万名工人仅对应30台机器人,而韩国、日本、德国和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数字为437台、323台、282台和152台。
按照中国机器人发展五年规划所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的机器人密度将达到150台以上,预计3~4年内中国机器人应用规模将高居全球第一。
但在如此有诱惑力的市场中,掌握话语权的是“四大家族”:瑞士abb、日本发那科公司、日本安川电机、德国库卡。除了第一梯队的“四大家族”,许多机器人海外制造商,也都已经在中国进场布局。
目前,“四大家族”占据全球工业机器人6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研发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国内厂商还没有叫阵“四大家族”的实力。
“在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零部件中,国产控制系统能基本满足目前需求。但如果要进入汽车领域,对控制器要求更高,控制器还是需要进口。伺服电机跟控制器差不多,低端没问题,中端产品也能满足要求,减速机问题最大。”宋晓刚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中外品牌减速机的原理设计基本一致,但在工艺精度和稳定性方面差距非常大。
“减速机由几十个小零件、齿轮组成,不同的材料、温度、加工速度都会有影响。每个加工精度提升都要靠技术累积,更重要的是靠加工工艺的摸索。”宋晓刚说,目前一些国产品牌已经能实现小批量生产,比如南通振康,2016年销售达到1.2万台,而排名世界第一的日本纳博特斯克年销售量是25万到30万台,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大批量生产条件下,如何保持产品性能和精度的一致性,是本土品牌的短板。”
除了靠时间积累,在技术路线上另辟蹊径也是国产品牌突围的一个现实路径。对金石机器人而言就是如此。
“桁架机器人有别于关节机器人,核心技术我都有,甚至我有的,国外都没有。”刘金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桁架机器人中最核心的是导轨技术,最早用于战舰,要求20年不能变形、稳定性要求极强,“这种导轨国内没有,材料也没有,我们跟德国人买,德国人也不卖。”
从德国买成品,分析镜像,做出原材料,再到最难的热处理环节,刘金石带领公司研究团队摸索了6年才攻克难题,“导轨都是一米一米拼接而成,要求不能有接缝和累积误差,非常难,但现在我们能做到拼接200米长。”
传统关节机器人应用在汽车制造领域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但目前基本都被国外品牌占据市场,国内自主品牌很难分得一杯羹。
“关节机器人,负载一般在300公斤以下。超过300公斤的重型关节机器人,能造的厂商非常少,即使能造产量也在几十台,产量极少。”刘金石说,而桁架机器人的最大优势就是超大负载,最大的能抓起4吨重的东西。
“目前瑞士的厂商能做到负载2.5吨,德国的利勃海尔能做到1吨,而我们能做到4吨。国内做上吨重机器人的成熟案例没有,就我们一家。”刘金石说,做4吨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完全实现柔性生产和无人工厂,“传统物流全是在地面,地面轨道线、叉车,全是在地面跑。而无人工厂的物流都是在天上,设备在上方自由穿梭,能实现全厂的柔性化生产,可以在超大空间内行走,而地面是留给人维护设备用的。”
“我们定义的无人是生产环节不能有人,生产环节的原材料搬运、上线、出线、检测、包装,一个人都没有。”他说。
绕开关节机器人,主攻桁架机器人,在刘金石看来,也是国内品牌最有可能“干倒”国外品牌的领域,“国外在技术积累方面有经验,不代表工程能力很强。我们给用户做工程4到6个月,超过一年的项目都很少,但国外做一个项目需要2年,而且价格让人很难接受。这方面是我们的强项,跟高铁非常类似,是系统工程。”
扎堆低端的“雇佣军之忧”
今年两会期间,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自主品牌方面,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大多还都是一些中低端产品,六轴以上多关节的机器人供给能力相对较低。”
这也意味着,从行业最高主管部门层面,确认了对目前行业中“高端产业低端化和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风险”的担忧。
在这个行业里,这种“雇佣军之忧”并不是最近才有: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无序竞争局面开始出现,相当一部分企业以集成组装生产为主,停留在模仿、跟随和简单集成阶段。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2016版)》显示,国产工业机器人以中低端产品为主,主要是搬运和上下料机器人,大多为三轴和四轴机器人,应用于汽车制造、焊接等领域的六轴或以上高端工业机器人市场主要被日本和欧美企业占据,国产六轴工业机器人占全国工业机器人新装机量不足10%。
另一个滑稽的现象是,在近年来很多展会上,原本是智能装备的工业机器人,却被用来表演唱歌跳舞,而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种表演“既谈不上不智能,也没有核心技术”。
在宋晓刚看来,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国有品牌附加值不高,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导致成本高、利润低。另一方面,目前进入机器人行业的门槛其实很低,“机械手臂可以外协(外协采购)、控制器可以买到,精密减速机可以买到,伺服电机可以买到,甚至应用软件都可以找别人来开发,这就相当于你这家企业只是组装了一台机器人。”
常州铭赛机器人也曾经走过这样一段弯路。铭赛属于典型的高校教师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企业,创始人曲东升原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
“2014年之前,铭赛的产业化成果转化过程很不顺利,那时公司觉得什么都能做,什么项目都接。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几年下来,除了盖了一栋楼,在技术沉淀方面毫无成果。”铭赛董秘蒋筱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铭赛最早是做扬声器的点胶机,“但现在做点胶机的人遍地都是。”
在蒋筱霏看来,点胶机就属于典型的过热产业,“这块产品对精度要求不高,行业门槛也不高,但毛利率在40%很正常,导致很多投资者开始涌入投资。当需求和供应不成正比,就开始打价格战。”
从2014年开始,铭赛决定转型。蒋筱霏说,转型的方向,首先是市场容量要足够大,“其次,我们会考虑技术壁垒是不是足够高,不是哪个土老板,有钱就能砸进来的。”
铭赛最终选择了个人媒体终端设备,比如手机的核心部件的智能生产设备作为发力点。蒋筱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机零部件的生产设备对自动化要求相当高,比如从2016年开始流行的双摄,以前都是单摄。这样一来,原有设备完全跟不上节奏。每一个摄像头模组里面都有马达驱动,非常精细,人的肉眼完全不可能操作,全要靠机器。”
手机等智能终端的快速迭代也为这个领域的智能装备提供了大量商机。以摄像头模组为例,全国最大的生产商舜宇光学科技,一年更换设备就会产生2000万元的订单。
扎根微精密行业只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给铭赛带来的变化非常明显。2014年以前营收一直在3000万~4000万元徘徊,2016年突破了6000万元,2017年预计将达到7000万元。
“目前铭赛在本土品牌中间没有竞争对手,就是用来代替进口设备。” 蒋筱霏说,这个领域以前都是采用进口设备,以一台做马达内部连接的普通设备为例,进口一台国外设备要30万元,而铭赛的只需要15到20万元,“我们正在进军线路板,这是手机自动化里最难攻克的部件,国外设备要卖到170万元,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始验证,大概在70万元左右。”
在蒋筱霏看来,这个领域决定竞争力的,其实并非核心零部件,而是对客户工艺要求和精度的把握,“最核心的就是掌握客户的工艺,有什么步骤、特点、要求,如果我不是熟悉你工艺的技术开发者,开发不出好的产品。”
这些来自企业生产一线的感受和宋晓刚的判断完全一致。在他看来,机器人的传统应用领域是汽车,国际上几大巨头的产品主要应用在汽车领域,但国外并没有中国这么全面和细分的制造业门类,国外机器人品牌也不可能熟悉这么多工艺流程,“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本土品牌应该对不同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工艺、流程、管理更加熟悉。”
对于未来,宋晓刚判断,今后本土机器人企业中,零部件和机器人本体都将是逐渐淘汰的过程,因为这个方面很难撼动国外品牌的优势,“但我们需要一大批了解机器人性能、熟悉细分行业工艺的系统集成商,这是国产品牌可以发力的方向。”
防止非理性泡沫
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主战场,而落地后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将工业机器人列入大力推动突破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工信部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完善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系,产业销售收入超过3万亿元,实现装备的智能化及制造过程的自动化。
“这不是政府忽悠起来的,而是市场本身最先反应,确实有强大的内在需求,随后国家鼓励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相应政策跟上来了。”宋晓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各地区都扎堆布局,不仅制造企业,甚至金融界对机器人产业都非常关注,一哄而上的现象已经开始显现。
“全国有20多个省市把机器人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培育、推进发展,全国已建成和在建的机器人产业园区超过了40个,短短几年时间,机器人企业的数量超过了800个。”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两会上确认了这一数字。
目前布局工业机器人的产业地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的广州、佛山,长三角的上海、昆山、常州武进,环渤海区域的沈阳、青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安徽芜湖和重庆。
不少地区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比如,广州提出要建全国最具规模、最具竞争力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基地之一,2020年的目标产值是超1000亿元。重庆也提出要建国内重要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基地,2020年的目标产值也超1000亿元,深圳则将“工业机器人跨越工程”列为重大工程之一。
对于常州这个身处长三角的三线城市来说,如何定位自身的机器人产业布局,也有喜有忧。
“常州武进国家高新区目前机器人相关的上下游关联企业,有14家。去年工信部发布一个数据,机器人四分之一产量在常州。”武进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工信部发布数据,2015年我国机器人产量达32996台(含外资品牌),而常州市经信委的统计发现,2015年常州市机器人产量超过了8000台。
在她看来,与省内的苏州、无锡等城市相比,常州更加注重本地的工业制造基础,民营经济实力比较强,而且职业技术教育非常发达,能为本地机器人产业提供大量的产业工人和高级技工。
“四大家族”之一的日本安川、在精密减速机生产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纳博特斯克都选择落户常州。在宋晓刚看来,一些顶尖外资品牌落户之前,会特别做几件事情的调研,一是环境,主要是投资环境;二是市场;第三是配套能力。“常州位于长三角,既可以覆盖广泛的制造业市场需求,又具备很好的工业基础和加工配套能力,具备发展工业机器人的优势。”
忧的是,以一个三线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如何能吸引到发展工业机器人所需的高端人才。铭赛公司董秘蒋筱霏坦言,铭赛从原来粗犷的点胶,进入微精密行业后,对于视觉和软件人才的需求非常大,但现在运行发现,常州基础条件跟不上,人才很难吸引过来。“三线城市本身对人才吸引力有限,另一方面产业在升级、相关环境升级都需要沉淀。”
“如果是以旅游和服务业为主的地区,或者缺乏工业基础和配套能力的区域,我们绝不鼓励这些地方发展工业机器人。”宋晓刚坦言。
在这场机器人产业“竞赛”中,地方政府的补贴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筹码。例如,安徽芜湖在2014年出台了《芜湖市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若干政策(试行)》,其中细致地规定了十多项政府支持和补贴措施,例如,有对贷款利率的补助,“对本市机器人产业龙头企业的关键核心项目利用国开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给予贷款基准利率的50%贴息补助,期限两年,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还有对扩建厂房的补助,“二层厂房按300元/平方米补助,三层厂房按400元/平方米补助,四层及以上厂房按500元/平方米补助。”
在吸引人才和项目方面则规定,“支持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在本市设立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经市政府批准重点支持的,每年每所安排不高于1000万元的补助资金。” “企业将机器人研发总部迁入本市,研发总部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000万元(不含土地)的部分,给予投资额20%、最高1000万元资助。”
“政府的补贴政策取向没错,但一定要补助那些质量合格、真正在生产线上应用的机器人。”宋晓刚表示,现在一个最大问题是,相关政府部门,补贴政策不够精准,大水漫灌,导致一些机器人生产企业靠补贴“过日子”,甚至顶着机器人概念套取地方政府补贴。
“现在,让各级政府和产业部门去了解哪个产品是合格的也有难度。”宋晓刚说,从机器人产业联盟的角度,目前最关注的是建立行业标准和第三方检测认证平台,“政府今后就会采信这个标准和检测,重点支持的方向也会更精准。”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也表示,工信部和各省制定了分省市的差别化实施指南,还有通过制定工业机器人的行业准入条件,提高准入门槛等一系列政策,防止工业机器人的非理性泡沫。
如果您有机床行业、企业相关新闻稿件发表,或进行资讯合作,欢迎联系本网编辑部, 邮箱:skjcsc@vip.sina.com





